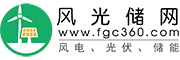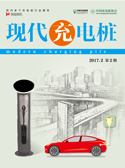由于電動化轉(zhuǎn)型大潮來得突然、能量大、時間短,之前還在潛心提升燃油機能效、降低汽車重量和風阻的傳統(tǒng)汽車企業(yè)被打了個措手不及。曾經(jīng)以控制車輛成本和利潤自傲的汽車制造商,在新能源汽車電池領(lǐng)域幾乎喪失了話語權(quán)。
特別是在當下中國,由于新能源汽車補貼直接與特定電池制造商掛鉤,包括上汽、北汽、江淮等主要汽車制造商旗下的新能源板塊,仿佛都在做同一件事情——給以寧德時代為代表的電池企業(yè)“打工”。
這成為汽車企業(yè)不愿推廣純電動車的重要原因之一,因為它們可能要把一輛車50%左右的收入分給電池企業(yè)。然而,在日益嚴格的排放標準和“雙積分”政策下,車企不得不投身新能源車領(lǐng)域。但它們能控制成本,掌握主動權(quán)嗎?
車企明顯“受制于”電池供應(yīng)商
短短幾年內(nèi),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新能源車市場。中國汽車工業(yè)協(xié)會數(shù)據(jù)顯示,今年上半年,中國新能源車銷量為19.5萬輛,同比增長14.4%。
值得注意的是,在銷售排名前10的新能源車企中,除了比亞迪可以“自給自足”,其他企業(yè)無一例外,都要向第三方電池制造商采購電池或電芯。
雖然不少企業(yè)號稱擁有“三電”(電池、電機和電控)技術(shù),但即便其能組裝電池包,其中重要的電芯仍依靠對外采購。
目前,北汽新能源、上汽乘用車、眾泰汽車、江淮汽車、吉利汽車等自主車企,甚至包括華晨寶馬等外資背景的車企背后,均有同一個影子——寧德時代。
作為國內(nèi)最大電池供應(yīng)商,成立僅6年的寧德時代迅速擴張,2016年產(chǎn)量達到6.8GWh,位列全球第三;今年上半年,該公司國內(nèi)市場占有率達到20.98%,超越比亞迪成為第一。
目前,電芯在汽車動力電池成本中占比最大。大眾汽車集團MEB項目報告顯示,在2016年這個時間點,電芯成本占50%,模組成本占13.3%,制造成本占36.7%。
這意味著,即便車企自己做模組和組裝,仍要為電芯付出高昂成本。由此,曾對供應(yīng)鏈占有主導(dǎo)權(quán)的汽車企業(yè)為寧德時代等電池供應(yīng)商“打工”的說法,并非戲言。
進一步說,這些電池供應(yīng)商,或許也只不過是在為另一些企業(yè)打工。
電芯的成本由原材料成本和組裝成本構(gòu)成。例如18650型電芯,其原材料成本占總成本近80%,組裝成本僅占兩成。
鈷是鋰離子電池的關(guān)鍵原料。制造這類電池的消耗已占到鈷金屬全球消費總量的42%。過去一年間,鈷的價格翻了一倍;分析人士預(yù)計,到2030年鈷的需求將增長30倍。
車企“倒逼”電池供應(yīng)商降成本
按照這一邏輯,在新能源車領(lǐng)域,車企幾乎被電池、電芯原材料等上游供應(yīng)商扼住了咽喉。其中利害,整車企業(yè)自然非常清楚,在確定電動化趨勢不可逆后,部分企業(yè)開始聯(lián)合產(chǎn)業(yè)鏈上的其他企業(yè),加大研發(fā)力度,降低電池成本。
電池供應(yīng)商對這一點感受最深。誰能生產(chǎn)更高品質(zhì)、更低價格的電池,誰就能占領(lǐng)市場。雖然實力更強的外資電池制造商被排除在外,但寧德時代曾表示,其每年研發(fā)投入為銷售額的5%~6%,到2020年之前,要投入超過300億元用于研發(fā)和升級產(chǎn)能。
寧德時代希望通過擴大規(guī)模、技術(shù)研發(fā)升級和上下游合作三重方式控制成本。
據(jù)彭博社統(tǒng)計,2010~2016年,電池成本下降了65%。未來,電池成本可能繼續(xù)降低。有人預(yù)測,2020~2030年,純電動車有望實現(xiàn)商業(yè)化普及。在此之前,除倒逼電池供應(yīng)商,車企還會采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捆綁電池供應(yīng)商,降低成本。
比亞迪的自產(chǎn)自銷自不必說,北汽與上汽選擇與寧德時代成立合資公司,也是一種探索;吉利與科力遠合作,同樣是降低新能源車成本、多路徑管控風險的方式之一。
通過各種各樣的合作,車企可以和供應(yīng)商形成更緊密的捆綁,從而降低整車成本、經(jīng)營風險,實現(xiàn)利潤最大化。供應(yīng)商也可以快速壯大規(guī)模,占領(lǐng)市場。
新能源汽車時代的提前到來再次證明了一件事:如果一家企業(yè)不具備核心技術(shù)且不做前瞻性布局,那么,它只能淪落到為人“打工”的境地。